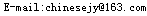人的名字本是一种符号,叫得明应得响即可。如果说仅仅“琴棋书画”而已,别无深意,也不过文人雅趣,信笔拈来,却也无足深思。却不料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一经融进《红楼梦》,竟变得令人不敢妄下断语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入画的主人惜春。这个女孩子孤介顽执、冷僻入骨,是一个很不合群的人。她的最大嗜好,恰便是绘画。这一点在小说中曾大事铺张过,给经的印象极深,似乎无须再来唠叨了。
而探春呢?除了精明强干,理家治人颇有方略外,于咏诗一道也只平平。但如果观察得稍细一点,她的喜欢书法是很容易看出来的。“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中对探春房中陈设有这样一番描绘:
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 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付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
这样的摆设,一望可知是书法家的派头。
如果这尚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再请看第三十七回探春致宝玉结诗社的帖子:
昨蒙亲劳抚嘱,复又数遣侍儿问切,兼以鲜荔并真卿墨迹见赐,何惠爱之深哉!这大概就是刘姥姥看到的那帖“烟霞闲骨骼,泉石野生涯”的墨宝了——这里刚送去那里马上就挂起来,还能说是不爱好么?
惜春爱绘画、探春喜书法、那么司棋的主人迎春呢?我的答复是,迎春嗜围棋。只因为除了“送宫花贾琏戏熙凤”一回外,并没有正面描述她的这一爱好,人们不大注意她的这一特点罢了。
第二十二回“制灯谜贾政悲语”中,迎春的诗谜是这样写的:
天运人功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
因何镇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同。贾政看了说是“算盘”,迎春笑着回答“是”,遂成铁案。
但究竟是不是算盘呢?我却以为“不是”的,而是“围棋”。八O年十二月,我在给《红楼梦学刊》主编冯其庸教授的一封信中曾谈及这一问题,冯其庸同志亦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将原信摘录于下,以就教于读者(略有变动)。
“前去信言迎春所制灯谜诗,其谜底不是‘算盘’,兹作说明如下:
“我意应释为‘围棋’,因为只有围棋才能与此四句诗所述全部特征完全吻合。
“按算盘以木为框,隔以横木名曰‘梁’,穿纵杆十余名曰‘档’;梁上每杆贯木珠二,一以代五,梁下贯木珠五,一以代一。每档以十进位,同时依法计算。
“不须咬文嚼字,‘理不穷’这一特点算盘是具备的。但‘有功无运也难逢’就颇为费解,因为只有在每一粒算珠都有相逢的可能性这一条件下,这句诗才是有意义的。但现在无论实际使用算盘时还是不用时挂起来,每一粒算珠都有其固定的‘邻居’,不相邻的算珠无论怎样‘有运’也是碰不到一起的,而相邻的算珠无论怎样‘无运’也总要相逢的。‘纷纷乱’就更成总是了,算盘是一种计算工具,运算时有口诀、有法则,一个子儿也乱拨不得,怎么可以用‘纷纷乱’来形容?(局外人或可以为乱,局中人心里清楚得很)至于‘阴阳数不同’,用在算盘上也实在勉强得很。
“但如解为‘围棋’,那么所有不通之处均可迎刃而解。围棋盘纵横十九线,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黑白子各自有八十粒。双方执子着棋,变幻无极、层出不穷,自有棋以来无同局之盘,‘天运人功’在这小小棋盘上演出无数局面,还不是‘理不穷’么?具体到每一粒黑白子来说,虽然实际上都有可能在棋盘上相遇,但这是要靠执棋人的筹算的,确实既要有‘功’又要有‘运’才能与对应的子相逢;算盘有口诀法则,而棋子布盘却是有法而无则,攻左视右、声东击西、瞻前顾后、着法不一、千变万化;满盘上星罗棋布、死活不一,劫杀刺征、黑白势力狼牙犬齿——的确是‘纷纷乱’——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执黑(阴)、执白(阳)子的棋手掌握着棋子的命运,而他们运筹计算的力量和方法各不相同,因此才形成了‘理不穷’、子‘难逢’、‘纷纷乱’的局面。
“既然如此,为什么贾政说是‘算盘’迎春答‘是’呢?我想这是很简单的——因为贾政是她的长辈,而长辈是说不错的。假如是司棋猜‘算盘’,怕难免就要得一个‘糊涂’的考语了。”
当然,不应排除一个谜有几种谜底的可能,猜算盘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作为迎春之谜,除了我致冯其庸同志信中所举理由外还有一个心理上的依据。我以为“命运把一个人当作棋子儿摆布”要比“当算盘子儿拨”的说法要多少漂亮、贴切一些,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再,算盘是账房里的工具,不是闺房里的摆设。贾府一干公子小姐没有见过当票,不认识秤星儿,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和算盘绝缘,贾迎春一个深闺秀女怎么会凭空想起用算盘的形象造一个谜呢?
第七十九回,实际上直接披露了迎春的这一爱好。在她搬出大观园后,宝玉作《紫菱洲歌》云:
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靶荷红玉影;
蓼花菱叶不胜愁,重露繁霜压纤梗。
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
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当今手足情!前四句写人去楼空、草木摇落的黯淡姜惨景色;后两句直点与迎春惜别的手足之情。中间两句是回忆迎春在时的情景——永昼敲棋——现在迎春一去只怕此时香楼空落、点点燕泥要污了棋枰罢!试想,如果此物不是紫菱洲素日最典型、最经常的娱乐器材,怎么会引起宝玉的这种联想和感慨呢?
惜春爱绘画,但她并不是一个高明的画家;探春喜书法,但未见得字就写得特别漂亮;同样的,迎春之嗜棋,也并不说明她是什么八段九段棋手。曹雪芹写她们的这些爱好另有深意,除了这些嗜好符合她们形象的内在素质外,与安排她们未来的命运亦不无关系。“懦小姐”迎春真就像一枚棋子一样由着人捏弄,摆到了死地;即如探春精干、强劲、潇洒的风度,亦不能说与书法毫无关系;那惜春“独卧青灯古佛旁”的凄凉景象,难道不是一幅油画的绝好题材?
至于元春的抱“琴”问题,我以为复杂得多了,不是本文篇幅可以囊括的,笔者已拟专文阐述,这里就不刺刺不休了。